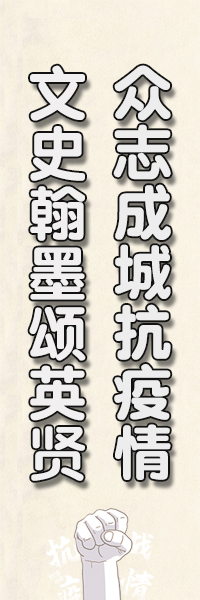采訪他,我的本本上只記下大半頁,十幾行字,他不太愛說話。那天在他家客廳,我倆并排坐著斷斷續續聊了約一個時辰。我當時印象是,身邊的他與我一樣,不高大,不再年輕,從容安靜。面對他的畫室,似乎不堅執也沒放下,整個人有些浸染藝術年久積重難返的樣子,沒有聚光燈下藝術家通常的蓬勃與激情,但內斂、謙和、儒雅。我猜,他從年輕時就追求的繪畫藝術,幾十年里,給過他多少歡樂,就給過他多少苦難,他顯然不是輕松玩玩繪畫的那一種人,他有著內心的堅守與追求。那天,窗外雨一直下,我離開時,他執意撐著傘下樓送我。回蕪后一個月,我沒動筆,雖然有些事耽擱,但不全是,一是想消化一些資料,二是看了那點資料也沒有頭緒,幾次坐到電腦前,敲不出字來。寫他不容易,他身上貼了兩塊標簽,一塊是“畫家”,他有美協頒發的證書,有許多意境美好的作品行世,成果被寫進《安徽美術五十年》;一塊是敬業奉獻的“好人”,同樣有官方頒布的文件,更有許多事跡材料支撐。但他告訴我,他一直是教師,美術教師。
我不想再給他貼什么簽,只是想讓你認識一下他,也許你會因此記住他的名字——杜樹森。我覺得杜樹森先生是一個值得走近的人,他心里裝著美與慈悲,還有因此而生發的對人生與藝術的獨特思索。我個人覺得,如果只論作品,他幾十年前就是畫家,他早年就有許多無意而佳呈現大美、直入人心的畫作;如果只論行善,他二十歲時就是一個好人,在林場插隊兩年,義務為村民畫像,特別是給那里的老人畫像,讓一生沒進過城市照相館的老人,百年后能給家人晚輩留下一分珍貴紀念......
繪畫支撐起青春歲月
1957年,杜樹森出生山東,兩歲多隨父母來到蕪湖繁昌。父親當過兵,轉業后做過公司領導、銀行行長,母親是普通員工。他走上繪畫的路,沒有家學淵源,是源于兒童時自己的熱愛。讀小學時正值文革,他經常為班級出墻報,畫刊頭,閑時給同學、朋友畫頭像。畫不像就找美術書研讀,反復畫,沒有人指點,畫多了,無師自通,畫啥像啥了。一個人繪畫需要這樣的努力,更需要這樣的天賦。
讀到高中,他所在的全班二十六人集體下放,他去的地方是繁昌境內黃滸上游一個林場,有些荒蠻,離縣城幾十里路,在交通不便的年代,算是比較偏遠之地。林場很窮,餐桌上只有米飯,沒有菜,知青們只能從家里帶些咸菜下飯。杜樹森生活用品不多,但他卻帶上心愛的畫具,畫畫填充了空洞的林場時光,也正是因為年輕,不畏天寬地闊, 不知晝短夜長。在林場,工人們干得都是粗活,采伐、修剪、防火、防蟲、工程建設......杜樹森做得最多的是植樹造林,首先要挖山,然后栽樹,植完樹從山下小河挑水到山上澆樹,反復如此,天天與滿山樹木糾纏,辛苦又單調。有一瞬間我有些宿命地尋思,他去邊遠的林場插隊,是因為他姓名中有很多木吧?杜樹森這樣的名字,不與樹木結緣才怪,后來他的畫中也常有各種各樣的樹木。此為說笑,也許當初起名時,了解命理八字的先生只是想為他增加一些“木”元素,以補其缺,也未可知。當然更可能只是父母希望他能成為天地間參天大樹,成為棟梁之材。
在浮山林場,幾乎沒有人會畫畫,這也使得能畫一手好畫的他鶴立雞群,名氣漸大。因為封閉,這地方的人,有的甚至一輩子都沒出過山,幾乎沒有人去過城里照相館。見他會畫畫,方圓幾里地,東一家西一戶虔誠地三請四邀,讓他畫像。休息日,杜樹森也不推辭,背起畫具走村串戶為鄉親們繪肖像、畫中堂。杜樹森的到來,仿佛改變了這個山沖人敘事風格,他們忽然關心起自己的模樣,關心起河流房屋在紙上呈現的樣子,更好奇起他這個外來的“知青”,憑一紙一筆是如何做到的,簡直就是“神筆馬良”。這里的老人們都想讓他畫張畫,將來走后能給兒孫輩留個念想。畫完畫,當然沒人付費,但純樸的鄉親們總是要留他吃頓飯的,而且桌上少不了平時舍不得吃的山鄉臘味,這類加餐總能恰好地慰藉杜樹森平日少油的胃腸。
有一次,林場幾里外一位老婦人去世了,家屬尋來,請杜樹森給老人畫遺像,靈堂上用。杜樹森從來沒有給死人畫過像,當時他還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大孩子,特別害怕面對死人,一時心里忐忑,不敢應承。未料來的那位老者朝他撲通跪下,對他說:求求你了,靈堂上沒張遺像不成呀!杜樹森見狀趕緊扶起老人,硬著頭皮帶上畫具跟老人走去。死者兒子把開始僵硬的母親扶起倚靠在床頭,杜樹森鋪開畫紙開始細致地對死者的頭部寫生,一直畫了幾個小時,最后將死者閉著的眼睛畫睜開,總算完成,出了一身汗。死者家屬看了,連聲夸贊:畫得像,畫得像。隨即,給杜樹森端來一碗面,碗底埋了三個雞蛋,杜樹森知道,這是貧窮歲月里鄉親們最高的待客禮節了。熱乎乎的雞蛋面條,也驅散了杜樹森的疲憊與緊張,他收拾畫具,獨自踏上林場的歸途。快到林場時,暮色四合,西天的光盛大厚實,樹林盡染,讓那個黃昏變得格外美好。不知何故,那一刻,杜樹森內心一掃生活中的苦難感,并對長長的未來,忽生期待。
在林場插隊兩年多,這里山綿延林茂密,小河溪流清澈,景色秀麗,空氣新鮮,雖難免遭遇蟲蛇,但更多是鳥語花香,是畫者天然寫生的所在。閑暇時,杜樹森成了這山林鄉間的獨行者,背著畫具,紅的花樹綠的草灘黃的沙丘,都是筆底過客,果林藤蔓青峰紫霞皆是紙上云煙,當然畫得最多的還是那些身邊人物:歷盡滄桑的老人、天真無邪的稚子、清純俏麗的村姑、英俊健壯的伐木工人……畫稿像日子一樣堆積,筆觸也是心到意呈。

那一個階段的杜樹森,對畫景物沒太上心,但山與樹的形態了然于心。他最喜歡畫的是人物,他覺得人物畫是繪畫最基本的東西,能畫好人物也一定能畫好景物,為此他還鉆研人體解剖學,了解人體組織結構。平時除了給別人大量寫生,也臨摹多種肖像,在人物畫上特別是對陳丹青、羅中立、周思聰作品沒少下功夫。沒成想這一側重為日后到來的美術高考打下堅實的基礎。
兩年后的1978年,恢復高考,大學開始招美術生,得此消息,杜樹森內心雀躍,幸運的是專業課考試內容是:頭像寫生、人物速寫、水粉,這正是他擅長的,在上初中時畫刊頭,已大量嘗試過水粉,所以考場里他如魚得水,結果以優異的成績被巢湖藝術學院美術專業錄取,從此杜樹森開啟了真正意義上的繪畫生涯,從業余走向專業,從民間走向科班。大學幾年,杜樹森如饑似渴,了解中外美術史,窺探嘗試多畫種,豐富繪畫理論,在學院陸君導師等指導下,基礎訓練更扎實更系統,人物水粉油畫均有了長足進步。畢業時,滿懷豪情的他本想去新疆支邊支教,對于他新疆是詩和遠方,但最終在導師勸說下服從分配,成為寧國師范學校的一名美術教師。
其時他與班上考進來的師范學生年齡相仿,學校美術教師資源稀缺,當時除了教學生,課余時間他還培訓學校美術老師,他二十平米的單身宿舍,成了免費的教室,也是在這樣的教學中發現了一些美術好苗子。后來他的這些學生苗子,有的成為美術界“名流”。比如擔任巢湖學院藝術學院院長、教授、著名畫家胡是平先生;比如哲學博士、清華大學美院培訓學院山水畫導師洪潮先生,現旅職文化部。他們在美術上都非常有建樹,如今工作雖忙,與昔日的老師杜樹森依舊彼此可言,精神共處甚多。此外他的學生,目前在省內外高校擔任教務主任、教授的,不下二十個,這讓一個當年的美術老師有多么欣慰!繪畫支撐起他整個青春,讓時光與丹青一樣絢麗。
他的畫有田園有故事更有詩意

為結束與妻子兩地分居,幾年后杜樹森從寧國師范調回繁昌三中,當時還叫繁昌環城中學,依然做著美術老師,校園環境優美,花木扶疏,在這里他一直工作到退休。從職業與事業重合度上來說,杜樹森是一個幸福的人,他一生追求的事業是繪畫藝術,他一生從事的職業是教授美術,教室、畫室、大自然,都是他的課堂,這對于一個熱愛畫畫的人,何其幸運!
這些天集中讀了些杜樹森先生的畫,被其中許多作品深深打動。我手頭的畫集是他的國畫集,沒有收進他的水彩與油畫,畫冊中作品以皖南鄉土風情為主,筆墨從寫實出發,體現的卻是浪漫與詩意,呈現出畫家心靈深處的記憶與藝術的理想寄托。畫家技法嫻熟,功力深厚,把人間平凡小景,描繪得詩意、鮮活,許多生動的細節,營造出安寧幽深的意境。他終日行走在天地之間,滿懷對大自然的摯愛,他表現的事物,表達的方式,有著自己的藝術性格特征,在體悟大地、生命、生存、繁衍和愛中,讓讀者感受到他的思索和藝術創造力。傳統的水墨繪畫中,不管是花鳥還是山水,其審美價值方面都與畫家對自然萬物的崇敬和熱愛有關。創作中畫家往往寄情山水、托物言志,透過山水、花鳥等不同的畫面物象,表達著內心對生命的感悟和理解。畫家杜樹森當然也不例外,他的山水、花鳥,各具風貌特點。其花鳥以寫意為主,“以形寫神”,力求“氣韻生動”;山水畫則多寫清新自然的山野鄉村,他熟悉這些描繪的對象,經過成年累月的細心觀察,畫出來色彩適度,筆墨造境中透出古樸清幽之意。
杜樹森說,我用線條訴說著不起眼的一草一木,我高興的是我的畫呈述的是一些真誠的故事,是對生命生活的尊重。他認為好的繪畫作品應具備:鮮明的風格,一定的繪畫難度,特別的情感寫真,要有前瞻性,有超越時代的審美能力。他常常想讓時間停頓下來,讓他能好好研究事物時空的一個切面,用不可思議的線條描述他發自內心深處的獨白。這似乎也是印象派繪畫大師的追求。所以說,以寫實為的杜樹森,是追求藝術表達的多樣性的。一個畫家,如果筆墨過于直白草率,不只是畫技問題,更是思維的簡單。

在杜樹森的畫集中,有一幅畫叫《青春的故事》,被很多讀者關注與評論,這幅畫也讓我眼前一亮,我覺得此畫也是作者自己的青春故事。畫面在黃金分割點有條小船,船頭坐著梳長辮著長袖襯衫的姑娘,其衣著打扮有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烙印,畫面被分割為兩部分,姑娘身后的河灘有茂盛的雜草、野花,幾條漁船,是她原生態的現實生活環境;而畫面右上角的通常應該是一片水域,有清清的河水,連通外面的世界。可是作者卻用濃墨填滿了本該空曠淺白的這個區域,濃墨中似有風云裹挾,密不透氣,又似乎有熱流涌動,奔突沖撞,這正是那個年代封閉鄉村的一種暗喻,迷茫,被禁錮,前面的墨色像烏云也像屏障。但畫家巧妙安排的人物,不是徘徊,而是靜靜看書,知識正是沖破眼前那片黑暗屏障的鑰匙。畫面上隨意播灑的點點彩墨,仿佛黑色天幕的星星,題為《青春的故事》,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過來的人一看此畫,都會心領神會。
在這幅畫中,作者一改單純寫景時的明快簡約,將思考、結構、邏輯、情感聚焦筆端,呈現出令人震驚的表現力!這樣的沉著冷靜的作品,最能體現杜樹森的藝術宣言。他說:“因我的繪畫存在,世界有所不一樣,一天又一天,我在尋找生動的生活,人與景不同的狀態,面目新穎或陳舊,豐富或單調,畸形或端正,我從自己的視角出發,觀察與表現人間豐富百態。”杜樹森始終以為,現實生活是創作源泉,永遠要腳踏實地,行走山水之間;物質材料是創作媒介,可以進行多種嘗試,因勢而為,為我所用;藝術想象是思維方式,沒有想象思維的高度,不會創作出有沖擊力的畫作;審美情趣是藝術修養,培養審美能力,克服自身習氣,是畫家畢生的修煉。
在杜樹森的繪畫中,有相當一部分是表現田園與家園的,比如 《春情》、《家園》、《山鄉春色》、《風很輕很輕》、《江岸秋色》等等, 小溪邊幾頭水牛,老屋前一條黑狗,小橋邊幾棵古樹,水跳上洗衣村姑,炊煙裊裊,暮靄沉沉,晚風習習,細雨綿綿,柴堆瓦舍,遠帆飛雁,甚至門前晾曬的花衣裳,每一樣風景,一經他點染就活起來,在眼前,在記憶中,在情濃深處,令人掩卷沉思,余音不盡。他的這些畫,有氣息,有節奏,有發現,有表現的角度,讓你感到,對于他而言,所有的時光都沒有白過,那些他經歷的事物風景慢慢發酵,怦然轟鳴,灑落宣紙,點墨成金。他的故鄉,他的田園,每一件事情都在慢慢生長,根越扎越深。當一個畫家想得越多的時候,他的畫就會體現出復雜,就會呈現一種厚度,我喜歡杜樹森的畫,有真情,有個性,有時代氣息,有藝術品位,有深度與廣度上的發力。人與人之間突然懂得,有時并不復雜,可能只是簡單的一面,只是一場靜靜的閱讀,我是在靜心讀他的畫時,突然懂得他的一些心思。
撫摸他的畫集,讓我感到作者自己在回望繪畫創作時,其實是在回望自己曾經歷的那個時代;當他在理解自我時,也是在理解這個世界。一個好的畫家,從來都是一個創造者。所以這些年來,他的畫受到無數人的喜愛,作品被大江南北收藏。他參與繪制出版安徽省美術教課書,作品多次入選安徽省重要展覽,藝術成就也被寫入《安徽美術五十年》史冊。他本人也擔任蕪湖市水彩油畫協會畫副會長,北京東方畫院副院長,取得這些成績對于一個長期生活在基層的畫家實屬不易。但我相信,在杜樹森精神世界里,早已看淡了很多虛名。如果說繪畫與生活還能讓他困擾甚至痛苦,一定是覺得自己還沒有達到內心期望的藝術高度;或者是現實世界還沒有讓他獲得哲學的從容。我讀到他寫的幾行詩:
我熱
我燃燒
我奔上了懸崖
我沖出了溫暖的懷抱
我揮動赤色的心
高歌在蒼茫的地平線
我分明能感到他對藝術火一樣的青春激情。而在另一首詩中又換了韻腳也換了旋律:
我乘上絕望的孤舟,
去尋找那消逝的希望,
在無情的汪洋中漂流漂流,
做個憩息的夢,
我不愿再醒來,
不醒來,
太陽就在身邊,
夢中又見希望。
在這里我又讀出了他人到中年后的“藝術苦難”,這是所有懷著使命感的藝術家共同的特質。我們擁抱藝術時抱得那么緊,如果藝術回抱我們時沒有同樣的力度,我們難免感傷。
他向我坦言道:我有點抑郁,是因為看到了很多不愿看的東西。一路走來,東張西望,忽然發現社會形態并不完美,發現人類的某些可惡。走在街上,放眼望去,羊肉館牛肉館林立,人們吃著它們的肉,滿嘴流油,談笑風生。追憶起人類農耕時代,生產工具落后,是因為有了牛,才幫助人們走過漫長的農耕歲月。生產工具進步了,人類再也不需要牛了,很快人們忘記了牛是我們的朋友,對牛揮起屠刀,由此可見,人類是忘恩負義的動物,世界要想安寧,人類必須自省。

你了解了這些,才能明白,杜樹森為什么那么喜歡畫牛,在他的筆下牛與人,牛與自然無比和諧,畫面不經意間充滿慈悲。有一幅叫《草青青》的牧牛圖,用筆簡潔,牧童騎在牛背上,牛兒在河難吃草,背景是大塊潑墨,灑點在畫面的青綠,透出春天的氣息,牛是
自由的,牧童也是自由的。這樣的畫鮮活,透著愛與生命力。現在很多收藏人,只擇畫家的名頭,他們已沒有耐心去細細品味畫的意境,也沒有能力鑒賞畫作本身品質,這對于繪畫藝術,算是一種可悲吧。
我有一位文友大姐,她也喜歡杜樹森的畫,她說:看他的畫,有些滋味說不出來,從審美上看并不迎合觀眾。比如他畫站立的樹,空曠的天,遠處的山,背著籮筐的少年......這些就好比文章中的一段白描,沒有華麗的句子也沒有跌宕的劇情。但你能感覺到作者的體恤。能看見村莊溫情孤清,還隱隱約約看到了一種自然的宗教。我覺得這位大姐比我更了解杜樹森。杜樹森還創作過一幅油畫《春晨》,霧氣繚繞的新安江邊,一只有些年頭的駁船靜靜停泊,一只狗,靜靜安臥,成為最動人的畫眼。畫中有故事,杜樹森說,“那天,一個人出去寫生,走了大半夜的路,一只狗不知道什么時候跟在了身后,一直把我送到了新安江邊。”所以他就畫了狗,于是這只狗在《春晨》里也充滿靈性的望著我們,望得人心生暖意,那暖意其實就是畫者心底慈悲的流露,他筆下所有的動物,比如每一頭水牛,都有這樣的暖意,動物或景物都有這種愛的傳遞,總是讓人有無言的觸動,無言的心動。讀他的畫一多,你會覺得他其實是一位詩人。
用畫筆點亮一城的丹青夢

如果說創作是杜樹森的白晝,那么教學就是他的夜晚,二者共同組成他年復一年的繪畫時光。多少年來,杜樹森從來都把教書育人放在重要的位置,甚至高過自己的創作。除了學校里正常的教學任務,每周四晚上便去縣文化館公益教畫。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,那時文化館還很老舊,來上課的以少年為主。后來新館建成,教室更寬敞,來上課的成人更多了。他的課堂最受歡迎, 本來只標配三十人的教室,常常涌入五六十人。幾年后他的美術學員多到幾百近千,幾乎遍布小城的各個角落,學員中有教師、醫生、護士、會計、公務員、企業工人、個體經營者、退休老人,杜老師還把總部北京的東方山河畫院引來入駐文化館,并親任院長。
對于美術教學活動,杜樹森有他的理念與追求,他重視環境的培育改造;重視“情感的交流,大自然的陶冶”;重視繪畫時“個性的自由伸展,身心的徹底解放”。他的課堂常常延伸到室外寫生。
有位學員說:學習了一段時間繪畫技巧之后,杜老師安排我們走近自然,對景速寫。清晨驅車前往梅沖,“山水梅沖,十里畫廊”,這里山美、水秀,是東方山河書畫院的寫生基地。一行人在村莊、田野里,隨處都可以感受到無窮的妙趣。路邊,隨手摘下初夏季節里新結的半青半澀的野果子,洗凈可食。周遭有一種久違的親切而靜謐的氛圍。稻田一望無際郁郁青青,玉米正在吐穗灌漿,絲條、黃瓜長長的藤蔓沿著籬笆一直纏繞,在冷不丁的角落里開始偷偷地掛下清翠嫩綠的長條,辣椒、茄子、番茄趕趟似的在開花,遠處的格桑花和一年蓬渲染出一片清新和怡然……
你看看,這么美的寫生之地,哪個人筆底不會涌動激情。這就是杜樹森重視的大自然的陶冶,人與景物的情感交流。他讓那些幽秘的芬芳不被日常的庸碌和瑣碎所淹沒,能夠宛然呈現在學員面前。他指給學生的是另一條繪畫幽徑。

他打開畫具,邊畫邊說:同學們,這里一切皆可入畫,田野的一草一木,廢墟里的一磚一瓦,附近的柵欄、草垛、甚至垃圾桶。萬物洞觀,意在筆先,懂得勾勒、突出、取舍、刪減,力求在尺幅間寓深入于豐富。
他教得陶醉,學員們也陶醉。看她們寫的筆記:“我們披草而坐,醉于自然萬象,清風,流深,水窮,云起。每一點輕輕禽鳴、每一處細末微景,我們都會仔細聆聽和觀察,使心洞徹,天人感應,寵辱喜悲都在此一一放下。”
在跟隨杜樹森寫生的日子里,學員們感受是一致的:萬物美好,我在其中。
學員們還注意到,杜老師心地很軟,途中無論碰到受傷的鳥,抑或是遠離了水源的螃蟹,他都要給予幫助,他始終有眾生平等的宗教情懷。
在杜樹森的這些學員中,有一位女醫生遠在蕪湖,因為偶然聽到他的課,被深深吸引。幾年里工作再忙也驅車去繁昌上課,風雨無阻。她說:怕遲到,有時動身很早,但無論我多么早到,教室里杜先生總是已經在那里,一切準備就緒。
還有位學員,從小就跟杜老師學過畫,人到中年又續師生情縁,重新回到他的公益班學畫。她說:機緣契合,人到中年再遇幼時繪畫的啟蒙老師杜樹森真好,本來日日蹉跎,半生虛度,能夠再次提起畫筆跟杜老師學國畫,倍感珍惜。她們說:吾師——杜樹森,他的畫質樸、醇厚、篤善一如其人。我們師從杜樹森不僅學藝更是熏陶人格,所謂芳心向春盡,所得是沾衣。她們還說,杜老師經常教導,做人要中正至大,人正筆才能正,胸懷大了,筆墨自會不同。
在繁昌,許多文友畫友表示,日常微信圈里,總有杜老師和他的學生畫作被傳閱、轉發。這些年杜樹森也以一已之力,為他的學生們舉辦了三屆大型作品展。甚至國家文化部的某領導,因為是杜樹森的學生,也從北京特意過來為老師捧場,媒體也跟進報道,真是給畫展增加高光,而展出的那些質樸、靈動的畫作,雖有稚嫩,也很可觀。如果說,杜樹森用他的畫筆點亮一城的丹青夢,一點也不夸張。
有位退休學員說:愿丹青不知老之將至,讓老去來得遲一點,從容一些。杜老師教誨,國畫要求強調“外師造化,中得心源”。在繪畫中我希冀心靈得以自渡。研墨鋪卷,皴撮筆勢,點染色彩之際,“不思聲色,不思得失,不思榮辱,心無煩惱,形無勞倦”,我們把對萬物的洞觀凝于筆端,意存筆先,畫盡意在。而我之所求,畫不必完善,但能在貧乏、枯燥的日子里探尋一種生的意趣,足矣。

愿丹青不知老之將至,說得挺好,人總需要點什么來支撐生命所有的階段。我們是進入中老年后,才知道一生多么短暫,青絲與白頭挨得那么近。那天我看著杜樹森年輕時帥氣的照片,與眼前的他已判若兩人,加之筆者自己也年近花甲,內心不免感慨。杜樹森性格開朗的夫人笑著對我說,杜老師年輕時白白凈凈,英俊得很,身上散發出迷人的活力。這些年生病,要做血液透析,把他變老了,變黑了,沒以前那么精神了。其實在筆者眼里,杜樹森先生依舊很精神,只是多了些滄桑、沉穩,多了份長者風范。時光能帶走一些普通人,讓他們消失得無影無蹤,仿佛不曾來過人間;時光也會帶走一些大畫家,讓他們肉身消失不再有新創造,但永遠也帶不走畫家們留下的美和作品中呈現的慈悲。藝術與人性之大美,常存人間。(插圖作品:杜樹森)
作者:荊毅,本名董金義,中國作家協會會員,資深書畫評論人
編輯:陳燁秋